林语堂:有多喜爱苏东坡,就有多憎恶王安石
发布时间:2024-08-2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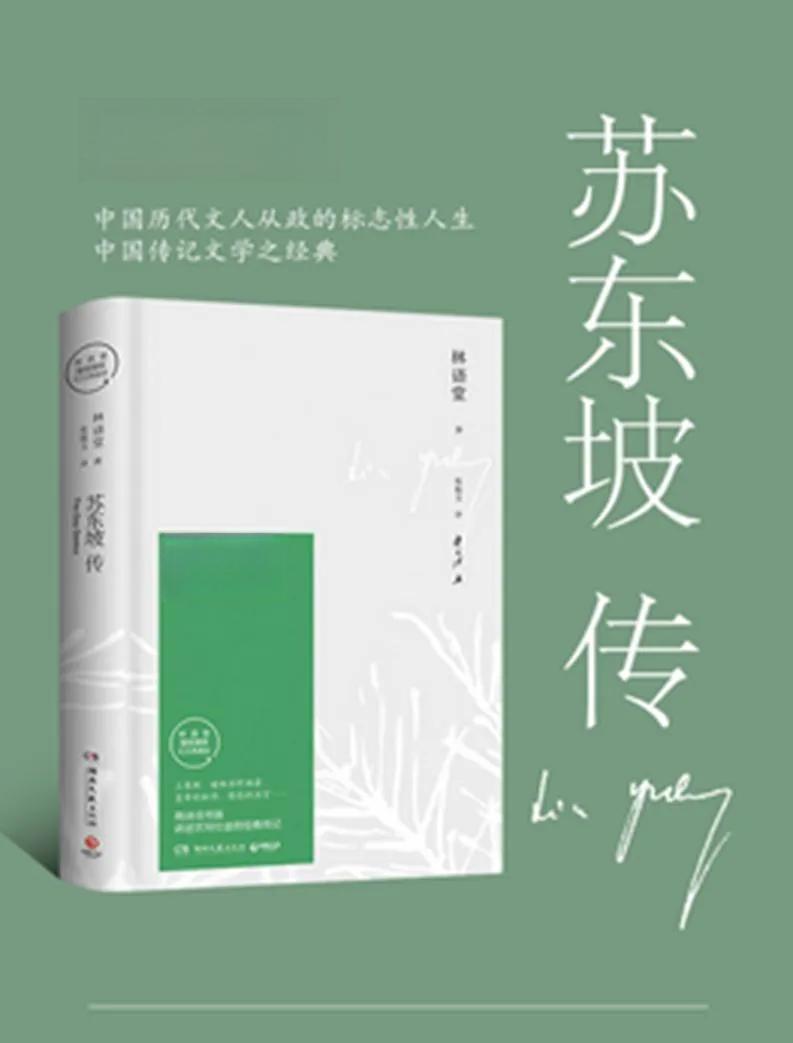
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,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在《苏东坡传》的序言中,他直言:“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,自然是一大乐事,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?”这种近乎偏执的喜爱,不仅体现在他对苏东坡生平的详尽考证上,更渗透在他对苏东坡人格的全方位赞美中。
在林语堂笔下,苏东坡是一个“秉性难改的乐天派,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,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,是散文作家,是新派的画家,是伟大的书法家,是酿酒的实验者,是工程师,是假道学的反对派,是瑜伽术的修炼者,是佛教徒,是士大夫,是皇帝的秘书,是饮酒成癖者,是心肠慈悲的法官,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,是月下的漫步者,是诗人,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”这种全方位的赞美,几乎将苏东坡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超人形象。
相比之下,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态度则截然相反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,他将王安石描述为一个“徒有基督救世之心,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”的人。更严厉的是,他将北宋国力的衰弱直接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:“宋朝国力之削弱,始自实行新法以防‘私人资本之剥削’,借此以谋‘人民’之利益,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,对国运为害之烈,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,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。”
林语堂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对比态度?这与他自身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密切相关。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,林语堂极其重视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。在他看来,苏东坡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格:才华横溢、洒脱不羁、不拘小节,却又不失道德操守。更重要的是,苏东坡在政治上坚持己见,但又能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。这种特质,与林语堂所推崇的“幽默文学”精神不谋而合。
相反,王安石在林语堂眼中则是一个专制主义者。他推行的新法,虽然初衷可能是好的,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严重侵犯了个人自由,导致社会动荡。林语堂将王安石比作“现代的精神病学家,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”,这种评价可谓极尽贬低之能事。
然而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林语堂的这种态度存在一定的偏颇。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,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能过于苛刻。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挽救北宋的财政危机,虽然方法上存在争议,但其改革精神本身是值得肯定的。
总的来说,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和对王安石的厌恶,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。他推崇个人自由、思想解放,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思想控制。这种态度,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,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情感,使得《苏东坡传》成为了一部充满激情和洞见的传记作品。